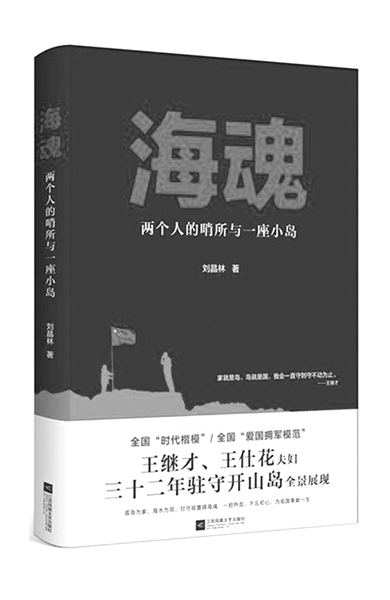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长篇报告文学《海魂:两个人的哨所与一座小岛》描绘了全国“时代楷模”“爱国拥军模范”王继才坚守孤岛、为国戍边的事迹,揭示出当代英雄的成长过程和心路历程。本报特约本书作者刘晶林,请他讲述背后的故事。
一
《海魂:两个人的哨所与一座小岛》这本书,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约我写的。他们约我以报告文学的形式,讲述中国故事,写守岛英雄王继才,不仅仅是对我的信任,也因为他们了解我,知道我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,作为一名军人,曾在离王继才驻守的开山岛不远的另一座面积只有0.115平方公里的达念山岛担任过连队指导员。也就是说,我对海岛生活,有过独特的体验。他们相信我在写作中会把曾经拥有过的熟悉生活和人生积累,顺理成章地融入到作品中去。
接受任务后,我即与王继才联系,准备进开山岛采访。可是在这之后的两个多月里,一直上不了岛。究其原因,海上风浪太大。我在岛上生活过,我知道春天海上的风刮起来没完没了。一般情况下,风连续刮上七八天,会停一停,喘口气,歇一歇,接着再刮。可是风停的间隙,涌浪是停不下来的。无风时的涌浪,一波接一波,从波峰到浪谷,落差很大。一般的船几乎无法行驶。涌浪把船忽而举上天空,忽而抛至水底,几个回合下来,即使是经验丰富的船老大,也经受不起这般穷凶极恶的折腾。接下来,还没等到涌浪平息,风又会接着刮了起来。
在这期间,有过一次进岛的机会,王继才联系了一艘渔船,并告诉了我开船的时间。燕尾港离我家90多公里。那天,我怕误船,凌晨三点起床,独自开车上路。结果快要抵达时,接到船老大电话,说风浪实在太大,即使开船,到了开山岛,也靠不上码头……
这样一来,我只好原路返回!
因为进不了岛,那段时间,我只好隔三岔五地通过电话,对远方的王继才进行采访。这种独特的采访方式,在我近五十年的写作经历中,还是第一次!
有时候采访之余,我会和王继才在电话里闲聊一会儿。比如,我问他岛上的情况,储备粮够吃吗?地里种的蔬菜受损如何?等等。王继才总是报喜不报忧,说一切正常。再问,他便转移话题,说在岛上住久了,风浪见多了,也就习惯了。
我知道他避重就轻,怕我担心。
我说过,我有过驻守小岛的经历。最初我认识海风的凶狠,是在达念山岛。那天,初上岛的我,在南山坡洼地里看到几棵柳树,它们的形状,可以说,就是风的形状。它们一律匍匐在地,枝条有序地朝着一个方向伸展,树冠一旦与山脊取齐,就不再长了;再长,就被风削去。再看树枝,没有直的,长度不超出十公分;超过了,注定就会被风摧残成骨折。过后树枝接着再长,再骨折……树干也是如此,扭曲着,体无完肤,伤痕累累。那都是海风施暴留下的印记。看着它们,恍惚间,你甚至怀疑那是树吗?柳树怎么是这个样子?它怎么可能与西子湖畔的那些秀美的同类共属一族?然而,它们确确实实是树。它们生长在远离大陆的小岛上,生长得惊心动魄,生长得无比艰难。如果用文学的语言形容,它们分明是风的活化石!
在岛上,久经风吹的树是这样子,那么,人呢?长年守岛的王继才都经历了什么?这是当时未能进岛采访的我,迫切想知道的。
二
第一次见到王继才,是在数月之后。那时被困小岛多日的王继才,作为“爱国拥军模范”代表、特邀嘉宾,费尽周折,乘舟跨海,前来出席江苏省连云港市举办的庆祝建军九十周年文艺晚会。演出前,我对他进行了短暂的采访。
王继才和我事先想象的样子差不多,脸膛被阳光和海风镀得黑红黑红,守岛人的外在特征十分明显。交谈中,几乎是我问一句,他答一句。他的话不多,许多时候,仅是通过几个单词,来表达他要说的内容。说完,他会朝你笑笑,那意思是已尽力了,并带有抱歉的意味。我知道,那是他长年累月生活在特殊环境中,平日与他人很少交流的缘故。试想,驻守开山岛之前,时任生产队长兼乡民兵营长的王继才,不可能这样。如果当年的他如此不善言语,怎么去履行职责?所以说,他的寡言,是在孤岛生活久了渐渐形成的……一想到这,我的内心某处便隐隐作痛。
自然而然我会联想到当年驻守的达念山岛。岛上生活着清一色的男性军人。那年月,物质条件差,虽然连队有一台上级下发的凯歌牌黑白电视机,但海上没有信号,收不到节目。打开电视,除了噪音,就是满屏的雪花点。有一次,我出岛开会,没想到上了岸,人整个儿就傻了,为什么?眼睛不够使了。岛外的色彩太丰富,弄得我晕晕乎乎,目不暇接、眼花缭乱!接下来,我听到了一个声音,那是一个年轻母亲与孩子对话的声音。要是搁在现在,纯属生活中最普通的声音,即使听到,也会被过滤掉,不再引起你的注意。然而,对于远离大陆,久居小岛,恍若与世隔绝的我,竟觉得那声音美妙极了,是世界上最好听的声音!于是我下意识地跟在那个年轻母亲和孩子身后,为的是能够多听一会儿……
换言之,当时一个连队几十号人,我都被环境改变成了这样,何况王继才呢,他们夫妻二人守着一座面积仅有0.013平方公里的小岛,平日里连找他人说话的机会都没有,久而久之,语言功能能不退化吗?这样想来,我的心里就多了些许感动。
三
又过了一些日子,我搭乘渔船来到开山岛。不巧的是,那天有一个文艺团体上岛慰问演出,王继才很忙,一时顾不上接受我的采访。于是,受好奇心驱使,我来到伙房,看看是谁在那里张罗午饭。
在伙房,我见到了王继才的大女儿王苏和她的好朋友、一位船老大的女儿。因为上岛的人数较多,王苏告诉我,接到父亲王继才的电话,她和朋友提前购买了食材,然后和演出人员一同上的岛。我问王苏,以往岛外来人,都是你赶过来做饭吗?王苏回答,爸爸、妈妈忙不过来,需要帮手。
据我所知,最初王继才、王仕花夫妇驻守开山岛时,王苏还小,才一岁多。她是奶奶带大的。后来奶奶年老体弱,被她的叔叔接走,家里只剩下她和弟弟、妹妹。不得已,王苏小学5年级辍学在家,小小年纪,既当爹,又当妈,做饭、洗衣,样样活都干;除此之外,还要负担开山岛哨所的后勤保障,往燕尾港码头背米、背面、背煤、背采购来的蔬菜等等,托船老大捎进岛……当年我守岛时,在陆地负责后勤保障的兵力,大大超过岛上人员的编制。可是对于王继才、王仕花夫妇,情况却不一样了,他们在岛上的后勤供给,大多是由他们的大女儿王苏一个人完成的。王苏从十岁起,就肩负起小岛后勤保障的重任,即使是她后来结婚生子,参加了工作,仍旧兼职,默默地承担着这一项工作。
由此可见,英雄是个体,也是群体;英雄的呈现,是有条件的。在王继才的身后,站着他的老母亲、女儿、船老大,以及许许多多给予他支持和帮助的人。他们也是英雄,令人肃然起敬!
那天慰问演出结束后,我见缝插针,与王继才聊了一会儿。
王继才希望我在书中务必写上他的不足。他说他只是个普普通通的人,在守岛过程中曾经有过恍惚、犹豫、徘徊与动摇。他曾打退堂鼓,写过辞职报告,经身患重病的县人武部政委王长杰的开导和鼓励,他才有了之后的坚守……
王继才的话让我与他拉近了距离,我觉得他是英雄,也是常人,有着人性通常所具有的一些弱点。好在他能够不断地战胜自己。
作为一名作家,我深知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生命。所以采访中,我曾向王继才提出过质疑。我说:“守岛32年来,你们夫妻二人坚持每天升国旗,即使是有一次,你被狂风推至崖下,摔断三根肋骨,也没有间断。其实,在这远离大陆的小岛上,并没有人要求你们这样做。遇上恶劣天气,一天不升旗,又能怎么样?”我话中有话,是想问,这里面有没有夸大其辞,掺有水分?
王继才听了,不紧不慢地对我说:“开山岛往前就是公海。你要是在这里生活久了,也会像我们一样,天天升国旗的。”
我一下子明白了王继才话中的意思。是的,因为常年守岛,在岛上,领海、领空乃至整个国家,都变得非常具体,它可以是海上的一朵浪花,岸边的一块礁石,天上的一片云彩,或是远处的一点白帆……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,当王继才、王仕花夫妇把国家与自己的生活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,天长日久,内心的潜移默化,注定会引发深刻的变化,那就是家国情怀,舍小家为国家。所以说,在这样的前提下,他们每天坚持升旗,完全是出于内心的驱使,具有逻辑的合理性。升旗对于王继才、王仕花来说,不仅仅是一种形式,还具有一种深刻的内涵!实际上,他们已经把升旗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,就像人需要吃饭、喝水、呼吸空气那样,一天也不可缺失!
四
这就是我认识的王继才,他让我心灵震撼。后来,我把这种感受一一写进了《海魂:两个人的哨所与一座小岛》这本书里。
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新年贺词中说:“此时此刻,我特别要提到一些闪亮的名字。今年,天上多了颗‘南仁东星’,全军英模挂像里多了林俊德和张超两位同志。我们要记住守岛卫国32年的王继才同志,为保护试验平台挺身而出、壮烈牺牲的黄群、宋月才、姜开斌同志,以及其他为国为民捐躯的英雄们。他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,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。”
崇尚英雄,就是崇尚崇高,张扬一个强大国家、优秀民族的血性。守岛英雄王继才,我们不会忘记你,共和国不会忘记你!
(刘晶林,一级作家。曾获紫金山文学奖、江苏戏剧文学奖、中国影视家协会长篇电视片奖。)







